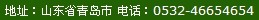|
几十年前入戏班时,正是戏曲的黄金时代,谁不曾幻想过自己在舞台上绽放光芒。现如今,日夜奔波于乡村集镇的简陋舞台,曾经年少爱追的梦,早在岁月的磋磨下化成戏台上一次次的身不由己。 这是一群既“苟且”,又践行着“诗与远方”的人。 戏台上,他们是风流潇洒的才子佳人,威风凛凛的帝王将相;戏台下,饮风茹雪的生活由乱砖碎瓦砌成,日常布满尴尬。 他们从边缘之地出发,挑担推车,扶老携幼,将古老的身形,夸张的脸谱,粗犷的唱腔,宣泄在空旷的田野中,对于这块土地的意义独一无二。 他们仿佛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,草根,质朴,沾满泥土气,辗转奔波,顽强生活,正变成一个摇摇晃晃的背影,在夕阳下渐行渐远。 他们可能不会突然“消失”,却在逐渐“消逝”。令人伤感的是,这个进程似乎并不可逆。 他们是乡村戏班,从历史深处走来,是“流浪”在大地上的声响。 01“散装”班底和“拼盘”演出 夜深了,天空开始飘起雪花,乡间小道曲折难行,黑黝黝的村庄里各式房屋影影绰绰,只能循着若有若无的乐器声前行。 转过几道弯,震天的音响和两个相隔数十米对立的戏台迎面而来,舞台前聚拢了不少看热闹的老乡。 在河南农村,按习俗,每逢神仙菩萨的重要日子,或者赶上家里办红白喜事,豫剧因其浓郁的地方特色,深受村民喜爱,成为乡村仪式上不可缺失的一道精神大餐。 今天的演出为的是孝子们给过世老人操办十周年,这在当地是件大事,一般要请戏班子来大操大办一场。有条件的家庭,会请两家戏班子唱对台戏,叮叮咣咣持续一个晚上加一上午,据说是为了请老祖宗好好过过戏瘾。 此时的舞台上,正演唱着戏曲选段《大登殿》。这出戏讲述的是薛平贵得到代战公主的援助,攻破长安自立为帝的故事。戏曲演员张国庆在台上唱完一段,绕到舞台车背光处抄着手休息。 这时,舞台上画风突变。《酒干倘卖无》的音乐从音响里嘶吼而出,五彩镭射灯来回扫射,在深夜的村庄里略显突兀,震得屋檐残雪直往下落。 近些年,很多乡村戏班的装备开始迭代升级。过去是一辆小皮卡拉着设备到处找土台子扎戏棚,费时费力。现如今配备了舞台车,车厢展开以后大屏幕等声光电设备应有尽有,极大提高了乡村戏班的演出观赏度。 一个身着短袖的女子走出来一阵热舞,连唱带跳穿插土味十足的喊麦,不断调动着台下的气氛。动感的音乐和歌舞表演明显更有吸引力,起码更易懂,喝完酒的中年男人听到动静后,三三两两走出家门聚拢在一起,舞台下的观众开始多起来。多数人穿着厚厚的睡衣,这在村子里似乎是个时髦的打扮。 观众多了,演员明显更卖力。女子拿起两瓶啤酒在地上使劲“墩”了几下,一口气浇在自己头上。随后,仰脖连“旋儿”四、五瓶啤酒后,跟着就是翻跟头接一个大劈叉,引来一阵惊叹。 短袖女子浑身蒸腾着热气,雪夜中大声喘息。来不及休息,因为舞台不能出现空档。她马上钻入一个羊毛狮头,开始一段南派舞狮表演。舞狮表演动作夸张滑稽,演员跳下舞台讨好般和观众互动,引来现场笑声连连。 连内敛沉默的老年观众都开始鼓掌,年轻人更是借着酒劲表情夸张地叫好。“看到了吗,这就是如今的乡村戏班,你得唱戏,还得能演老乡们爱看的热闹。”张国庆抿着嘴,回头说道。 从艺30多年,作为河南通许县非遗曲种渔鼓道情传承人,张国庆唱渔鼓道情的机会却并不多。 从清末盛行起始,渔鼓道情传承已有多年的历史。其形式是用三尺三寸长的竹筒,蒙上猪护心皮,配上木筒板拍打发出响音说唱。一人边演唱边伴奏,右手拍击渔鼓,左手敲击竹板作为伴奏。 很显然,在追求动感新奇有噱头的乡村演出市场,这样“寡淡”的表演有些乏味。专业戏校出身的张国庆,更多的是依仗早年摔打出的戏曲功底,游走于乡村各个戏班之中。 “她以前好像也是个唱戏的。”有人低声说。雪还在下着,夜愈发深沉,雪花在昏黄路灯下仿佛向上漂浮。锣鼓声还在响,狮子的大眼睛在飞雪中忽闪忽闪眨个不停…… 表演结束,我跑去后台,准备了戏曲演员转型、乡村戏班发展等好几个问题。女子从狮头中钻出来,浑身冒着热气,头发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汗水、雪水,还是刚才表演后残留的酒水。 面对这样一位“冒着热气”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演员,我努力压下自己的错愕,甚至为自己内心隐藏的一点鄙夷和不理解感到惭愧。那一连串关于乡村戏曲的严肃问题,显得那么高高在上,与当下的环境格格不入,令人难以启齿。 杂技吊铁环,魔术电锯切人,再穿插几段豫剧《王强点兵》《穆桂英挂帅》……快到夜里十一点了,演出终于接近尾声,掌班段琳霞过来喊大家吃饭。所谓掌班,就是本次演出的牵头人,一般是接到演出订单后,临时张罗来一套班子,戏曲吹拉弹唱,搭配舞狮杂技,还得管着演员们的吃喝住行。 事实上,如今绝大多数乡村戏班,早就没有所谓的固定班底,更多是呈“散装”形态。谁接到活儿谁牵头张罗,大家“凑份子”似的将演出承接下来。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团队和固定演出地点,大家为了生活不停奔波跑场。 按照规矩,办事的主家一般要为戏班安排一顿夜饭。吃饭的地方多少有点诡异:紧挨着搭好的灵棚,门窗大敞,跟露天野地没什么太大区别。两张拼好的小方桌上摆了八个“凉”菜(能结冰的那种凉),好在端上来一大盆热腾腾的面条,男人们开了瓶白酒,这似乎是难得的放松时刻。 大家围拢在一起,说着十里八村的乡里琐事,讨论着哪个演员演出效果好,哪个演员偷偷放录音对口型,哪个演员收入高,明天又要去哪里转场。看得出来,大家是临时相聚,但同行间又有着十足的默契。 雨雪交加的夜,穿堂风呼呼吹着,温度陡然降低了很多,夜饭却因为酒精的加持越发热闹起来。等到男人们脸色涨得通红且再三嘱咐我把他们写上报纸的时候,一旁静待许久的女人们开始起身张罗离开。 02乡村戏班之难 如今的戏班,还是从前的戏班吗?忍了很久,我还是问了出来。 “对于戏班来说,生存总是最重要的,你说是吗?”汽车行驶在乡间道路上,开始冒芽的树木不断往后移动,段琳霞坐在车后排悠悠回应我的疑问。 第二天上午的演出结束后,演员们分乘几辆车离去,后又在村郊一处麦地碰头。掌班段琳霞将刚刚拿到的演出款分发给大家。毕竟,“当着主家的面分钱,不太体面”。多年的学艺生涯,使这些戏班演员们虽然混迹乡野,始终保留着一份矜持。 但这份矜持,往往在面对生活时节节败退。 年轻时,张国庆、段琳霞都曾有机会进入到体制内的专业剧团,但都因各种原因错过了。说起来,至今仍觉遗憾。阴差阳错间,慢慢跑起了乡村戏班。 原以为职业选手下乡会带来“降维打击”,可偏赶上大环境惨淡。持续的疫情和乡村移风易俗双重压力下,大量的农村红白喜事演出活动被取消,不少乡村戏班断了收入。无戏可演的戏班陷入事实上的解散停滞状态,演员们不得不自谋出路。 好不容易赶上演出市场恢复,大家纷纷铆足了劲。可戏唱得再好,台下看戏的人依然越来越少。不止一次,张国庆演出时台下观众屈指可数甚至空无一人,但他依然全神贯注地将全套动作做足,“既然上去了,不仅要对得起舞台,更要对得起自己。” “农村人就图热闹,不管是雅是俗,热闹不起来以后就没人请你。”段琳霞坦言。乡村很多戏曲演员常面临无戏可唱的困境,所以即使是这样光怪陆离的乡村“拼盘”演出,也很少有人会拒绝。 为了接到更多的演出机会,不少戏曲演员常选择和唢呐、歌舞伴奏等乐手保持“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”,因为在农村,乐手更容易接到活儿,戏曲演员不得不依附于吹奏乐手争取更多的演出机会。 甚至于,随着人才的不断流失和经营上的困难,一些“草台班子”开始应付敷衍,先是减去了现场乐队改放伴奏,后来在演唱时“减词、跳词”偷工减料,更有甚者偷偷放录音对口型假唱。 一场无人观看的演出,为什么还要进行?事实上,如今戏班能够在乡村存在,是因为大家潜意识里觉得一场乡村仪式表演中应该包括戏曲,而并不是说有多少人那么爱看戏曲。请戏班参演,与其说是当下的消费偏好,不如说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心理惯性使然。 演出减少,观众减少,越来越多的戏曲演员生存困难。有的乡村戏班和演员甚至选择从事哭灵,这在民间是一种饱受争议的表演项目。 所谓哭灵,即戏曲演员披麻戴孝扮演成亡者子女的角色,在灵堂或棺材前且舞且唱,声泪俱下。有人认为从事哭灵会辱没先人、不太吉利等等,但不得不承认,哭灵收入确实比在戏班高很多。 “有人也请过我,但我不愿意做,主要是也做不来。”段琳霞说,“生活再难总有努力的道道,人不能让自己心里别着劲儿干事。” 疫情关上了戏班的一扇窗,直播能为戏曲传播打开一道门吗? 年,中国剧协副主席、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开通了快手账号。虽然他连
|
当前位置: 通许县 >ldquo流浪rdquo的乡村戏
时间:2022/6/12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能力作风建设年汇聚ldquo她
- 下一篇文章: 年,甘草干姜汤还能预防新冠吗
- 热点内容
-
- 没有热点文章
- 推荐文章
-
- 没有推荐文章